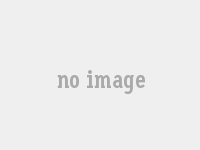桃花开了
李花开了
杏花开了
众神的花园——
群花开放,群鸟啭鸣
青草在我心里生长
一切皆有可能
撰文丨三书
春天找到我们
明,边景昭《春花三喜图》。
《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其一
(唐)杜甫
江上被花恼不徹,无处告诉只颠狂。
走觅南邻爱酒伴,经旬出饮独空床。
我们期待或不期待,到了该来的时候,春天就会来,花就会开。天地有信,岁序不言,世上的珍重事,有远比小小的爱憎更大的。
公元762年,春天来到浣花溪畔,之后又来了一百次,一千次,如今已经是第一千二百六十三次。这是真的吗?春天真的来了这么多次吗?春天一次次回来,到底是什么意思?
每年春天,我们仿佛再次置身于传奇故事,一个辉煌的开始。这个故事便是生老病死。出生的壮丽日子,死亡的痛苦日子,中间的一些日子。这即是我们的人生。这即是岁月,地球载着我们,绕太阳环行,周而复始。
我们会老去,会死去,但春天不会,春天永远年轻。或者说春天没有年龄,花年年开,草年年绿,如同永恒。春天一次次回来,好像在说,瞧,你又回到了这里。像一段回忆,反复播放,想要唤醒我们,让我们想起失落了什么。失落了什么呢?我们回想不起,且连失落感也失落了。
面对春天,我们总有些吃惊,春天永远新鲜,与我们永远是初见。春天使我们显得陈旧,我们正在衰老的身体,以及总是不安的内心。春天把一切忽然打开,使习惯了黑暗的人手足无措,恨也不是,爱也不是,无可奈何。
浣花溪的春天,比别处更烂漫,似乎故意要美给杜甫看。他是个多愁善感的人,又时刻想念着北方,“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李白这两句诗,用来描述杜甫的心情正合适。在《成都府》诗中,杜甫自己也说:“信美非吾土”,他就是这么固执。
他时常把自己关在屋里,锁在客愁里,但春色不管这些,“无赖春色到江亭”(《绝句漫兴九首》)。旅况无聊,却说春色无赖,他当然在说反话,别忘了,他还是个善戏谑的人。嫌花开造次,怪莺语丁宁,却实在拿春天没办法。
春色恼人,无处诉说,他想要与南邻喝酒,奈何对方经旬出饮,家中唯余空床。所有人都爱春天,所有人都在狂欢,花究竟开得如何,他也去江畔看看。此独步寻花之缘起。
被花朵击伤的人
清,王震《桃花群燕图》。
《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其二
(唐)杜甫
稠花乱蕊裹江滨,行步欹危实怕春。
诗酒尚堪驱使在,未须料理白头人。
被花朵击伤的人,春天不是他真正的敌人。春天爱所有人,但他已不是春天的人,他觉得自己不是。
此非杜甫独有的感觉,李商隐亦有同感。某天清晨,他起得很早,独自在帘间,庭前花开正好,莺啼若笑,他乃感慨而为诗曰:“风露澹清晨,帘间独起人。莺花啼若笑,毕竟是谁春?”这首诗就题作《早起》。
顺便说说我。不知不觉,我好像来到了时间的外边,不仅春天,四个季节都只是轮番经过。久居室内,已无所谓春夏秋冬,房间里绿植常在,瓶中四时花开,季节如同窗外的布景自动变更。我不觉得我是春天的人,也不觉得我不是春天的人。没有我,春天照样美满;没有春天,哦,没有春天,那将是所有生命的劫难。
杜甫傍溪行走,“稠花乱蕊裹江滨,行步欹危实怕春。”一个“裹”字,可见花有多繁,把整个江滨都裹住了。正因花繁盛,他走路不得不趔趄着身子,样子有点儿滑稽,实在可爱。
《诗经·绸缪》曰:“子兮子兮,如此邂逅何?”我们亦不禁要问,子美呀子美,三春花事无收管,该拿你怎么办呢?行步欹危,至极不堪处,他却忽作洒落,一摆手道:“诗酒尚堪驱使在,未须料理白头人。”别怕,有诗酒在!“驱使”有趣,好像诗酒是军队,是药物,供他调遣,帮他应对。
希腊诗人卡瓦菲斯写过几句诗,与杜甫有殊途同归之意。那首诗纪念公元六世纪的一位诗人,题为“科马吉尼诗人雅森·克林德的忧伤”,卡瓦菲斯写道:“我的身体和美都衰老了,那是/残忍之刀留下的伤口/我没有听天由命/我转向你,诗艺/因为你对药物有所认识:/试图止痛,在想象力和语言中。”
红花映白花
吴昌硕,《杏花图》。
《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其三
(唐)杜甫
江深竹静两三家,多事红花映白花。
报答春光知有处,应须美酒送生涯。
我们且跟上杜甫,一路寻去,前方像是百花潭。
“江深竹静两三家”,好个清凉的所在,江深竹静,人烟稀少,远离春天的热闹,他终于可以歇一会儿了。焉知又看见了花:“多事红花映白花”,这些花红红白白,真是多事,很得意似的,它们红白相映,不想说好看都不行!
好吧,不跟春天过不去了,不跟自己过不去了。既无可逃,那就把自己交给眼前的光景,家事国事天下事全都放下,暂时做一个春天的公民。
春天从不辜负我们,不责备我们,不要求我们。“报答春光知有处,应须美酒送生涯。”走着走着,他放松下来,春光慷慨无私,即使内心黯淡的人也被照亮。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世界总这样、老这样,而天地依然清旷,应该好好报答春光,在还能畅饮的时候畅饮,以美酒欢送生涯。
如果寻花七绝句是依次所记,那么杜甫独步的路线应由草堂起始,沿浣花溪往东南,走到百花潭公园,再到散花楼,东望少城,不禁奢想佳宴。从杜甫草堂到散花楼,不足三公里,走路约半小时,从前的郭外,如今是闹市区,散花楼在百花潭公园入口处,凄清寒简。
百花潭公园,我专为造访过,也在春天,毫无感触,就是个城市公园而已。树木苍翠,这里那里的花,曲径随处有,却并不通幽,人造景观的标准化毫无内容,鸟语花香如同这个词本身一样空洞。
并非我挑剔,那片风景确实离古代太远,离春天太远。看看那些瘫坐藤椅上搓麻将的人,那些遛狗的人,那些跳广场舞的人,以及无论哪个大公园似乎都必不可少、即使不运作也散发出金属喧嚣的儿童游乐场。
还有流经这一带的浣花溪,在唐代浣花溪别名百花潭,如今属于成都南河上段。一条流淌在野花芳草之间的河,与一条流淌在坚固的水泥堤岸的河,你知道那种感觉完全不同。
黄四娘家花满蹊
明,陈洪绶,《花蝶写生图》。
《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其六
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
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
因为这首诗,黄四娘为后世所知,直到今天她的名字还活着。说明什么?说明诗的不朽,诗比世上所有存在都不朽,比我们所有人都更真实。“屈平辞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李白说出了诗与现实的真相,杜甫心有戚戚,所以立志“语不惊人死不休”。
相比之下,作为纪念馆,杜甫草堂是个死去的地方。这里的一切都在表明,杜甫早已作古,早已面目模糊。木刻廊上的诗句,亦像纪念品,很少有人读。草堂可以有,但里面没有杜甫。杜甫活在自己的诗里,纪念杜甫最好的方式,就是读他的诗。
黄四娘是谁,我们没必要知道。读这首诗,从她门前的花蹊,仿佛见其人。“千朵万朵压枝低”,沉甸甸的花,千朵万朵,压弯枝条,戏蝶翩飞,娇莺自啼,春色如此明迷,她家门前都成了仙境。
杜甫草堂里有一处景点,导览牌上写着“花径”,从主路另辟蹊径之前,先过一道写意的木桥,桥畔卧着的大石头上便刻有此诗,字迹墨绿,倒是风致。路过打卡的人,无一例外,必与石上刻诗合影。也只有这里,还略觉亲切些。
去年四月在成都,节气已近初夏,坐在金河边,一棵茂盛的翠榕树下。河水清且涟漪,日色藻影,水上时见鹤飞,翠榕叶落如雨。一杯茶,一壶开水,一本诗集,一坐大半天,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我在成都谁也不认识,除了杜甫,他懂得我。
我也即兴沿河独步,近浣花溪公园的一段,溪畔种了很多花,但是开得太规整,缺乏“稠花乱蕊”的野性。我没有去寻花,却也在河边隔着一道铁栅,看见某户人家小院里,一架嫩黄曼陀罗花,像倒挂的喇叭,开得那样憨娈,那样好法。
我为之驻足,看了很久,曼陀罗花随风摇曳,似一阵缥缈的音乐。布谷鸟在某处声声叫,时间仿佛从未流逝,现在就是唐代,也是未来,春天永远是春天,岁序不改,物物皆在。
作者/三书
编辑/张进 何安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