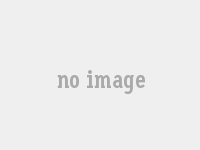转自:上观新闻
清代不设宰相,但人们对位高权重的尊者,往往也会在私下里称其为相,左宗棠即如是。左宗棠当年在捍卫祖国边疆,尤其是西征保卫新疆的战场上,建立功业,且载入史册。战场上的左宗棠为人称颂;但官场上的左宗棠,有时候暴露出来的某些缺点,却不足为训。晚清改良主义政论家、思想家薛福成,在所著《庸盦笔记》中记载,同为晚清有功之臣的曾国藩和左宗棠,后来因产生矛盾而至绝交。但即使如此,曾国藩在对西征中的左宗棠部筹饷及人马支援上,丝毫没有因为个人恩怨而受影响,仍不遗余力地予以支持。正是由于曾国藩的加持给力,因此大大提升了左宗棠率领的军队在边疆的作战能力,最后奏捷班师回朝。所以薛福成认为,左宗棠在疆场上立下的赫赫战功中,也有曾国藩不可磨灭的一份功劳。
然而令人不解的是,左宗棠对此却并不承认。不仅不承认,很多时候,他在会见部下将领时,还会当着他们的面责骂曾国藩。只是这些将领心里明白,左相这是心胸狭隘,意气用事。更扎心的是,他们同样也不认可左相对曾公(曾国藩)的数落,并且在背后发泄对左相的不满,说左相与曾公不和睦,有意见,但又“何必对我辈烦聒?”这些将领还认为左相的话“其理不直,其说不圆,聆其前后所述,不过如是,吾耳中已生茧矣”。
1872年3月,曾国藩去世,左宗棠终于在所拟挽联中检讨自己道:“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曾国藩)。”见此,将领们都欣慰地觉得,从今往后,左相应该不会再絮絮叨叨去数落曾公了。连薛福成也觉得,左宗棠“自此意气可平矣”。结果事实并非如此。就在左宗棠担任两江总督后,有官绅赴金陵(今南京)拜见他,左宗棠又故态复萌,交谈间不是忘情地讲述他昔日西征时的业绩,就是又开始数落曾国藩的种种不是。其间,薛福成还具体说了这样一件事:有个地方乡绅潘季玉,为公事赴金陵见左宗棠。可等他见到左宗棠,后者竟不给潘乡绅插嘴的机会,只顾自己说个喋喋不休,后来发现时间已不早,可能左也觉得累了,竟吩咐手下“送客”。想到第二天左要宴请宾客,潘觉得自己也在其中,便想那就等明天见了左再说吧。然而,第二天还是没有潘说话的机会。左甫入坐,“即骂曾文正公,继则述西陲之事,迄终席,言尚如泉涌也”。整场宴会俨然是左一个人唱独角戏。后来潘好不容易抓住了向左辞别的机会,想最后再向他陈述此来事由。但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左见了潘,还是一如潘几天前“初谒左相,甫寒暄数语,引及西陲之事,左相即自述西陲功绩,刺刺不能休,令人无可插话”。结果不难想见,潘这次见左终究还是无功而返。类似记载不独出现于薛福成的《庸盦笔记》,近代湘人欧阳兆熊在《水窗春呓》一书中也记载,一日左相在来客面前,“极(力)诋(毁)文正(曾国藩)用人之谬,词旨亢厉,令人难堪”。
毫无疑问,左在西征的疆场上身先士卒,奋勇杀敌,建立功勋,这是事实,且为历史铭记。但就因为左的高调扬己抑曾(国藩),以及屡屡在人前为己摆功,终至让人感到聒噪而厌烦,这也不无遗憾地影响到了左原先多多受人尊敬的人设。明乎此,便可知有些有话语权的职场人,平时能严以律己,谦逊低调;再加上谨言慎行,洁身自好,何以会被视为是难能可贵的美德。薛福成对左宗棠并无成见,他在《庸盦笔记》中记载发生在后者身上的这则故事,应该也是想让人们能从那些将领“烦聒”左相一事上,知道有所诫勉吧。
原标题:《陆其国:“烦聒”左相》
栏目编辑:华心怡 文字编辑:王瑜明
来源:作者:陆其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