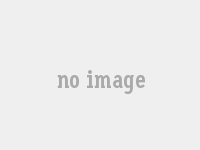“龙门一半在闽川”,福建在宋代已成为全国文化重镇,福建精神的核心特质在宋代也已基本形成,朱熹、郑樵二人正是福建人开拓创新、务实进取的典型代表,二人的关系也成为民间与学界津津乐道的话题。
郑樵(1104—1162年),字渔仲,自号溪西遗民,兴化军兴化县(今福建莆田)人,学者称之夹漈先生,南宋史学家、校雠学家。朱熹(1130—1200年),字元晦,又字仲晦,号晦庵,晚称晦翁,祖籍徽州婺源(今江西婺源),生于南剑州尤溪(今福建尤溪),南宋理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诗人。
郑樵与朱熹均为南宋时期福建文化名人,我们在田野调查中听到关于二人关系的种种故事,其中《朱熹访郑樵》的故事尤为生动。相传,某夏六月,朱熹去往闽南任职路过莆田,到萩芦江口时,只见山势磅礴、龙狮对峙,心想:“龙狮守江口,江上必有圣人!”于是溯江寻圣人,一路打听找到夹漈山。他上山去拜访郑樵,并提前在山门口的石头处下马步行以示尊重。郑樵会见朱熹,以“四白”即盐、姜、豆腐、水蓼四道“山珍海味”相待。二人相谈甚欢,朱熹随手写下“云礽会梧竹,山斗盛文章”一联赠送给郑樵,郑樵则赠送著作《诗辨妄》一书给朱熹。回去后,朱熹被郑樵隐居深山著书精神所感动,又派人送给郑樵一联:“三十年力学不下山,度量包罗天地;五百部著述曾诣阙,精神贯彻古今。”
以上故事绘声绘色,但也有其合理之处。陈宓《朱文公祠堂记》记载:“莆虽蕞尔邑,昔称士乡,先生初仕于泉,及淳熙间,凡三至焉。”可知朱熹至少三次到过莆田(含兴化县),第一次是南宋绍兴二十三年(1153年),朱熹从建阳赶赴泉州同安任主簿,路过兴化县,并去红泉听林光朝讲学。第二次是淳熙十年(1183年),朱熹应陈俊卿之请赴陈氏莆田家塾讲学。第三次是淳熙十三年(1186年),陈俊卿去世,朱熹赴莆田吊丧,并为之写行状。
朱熹第二次来莆田时郑樵已去世。据此,朱熹只可能第一次路过莆田时会见过郑樵,即绍兴二十三年(1153年)。是年朱熹24岁,五月赶赴泉州同安任主簿,约六月经过莆田,或在此时与郑樵相会。当时郑樵50岁,已献书宋高宗,名气较大,“举孝廉者三,举遗逸者二,皆不就”。朱熹拜访郑樵这位学术前辈也是情理之中的事,这才留下了民间“下马石”“四白菜”“延寿桥毁书”等传闻。
然而,关于此次会面皆不见于朱熹与郑樵的文集,甚至也不见于其他文献记载。因此二人是否会面,今已不可确考。但是,朱熹确实吸收、继承了郑樵的学术思想和创新精神,尤其是郑樵的《诗》学思想。关于《诗经》,郑樵作有《诗传》二十卷、《诗辨妄》六卷、《诗辨妄序》一百二十七篇、《原切广论》三百二十篇、《诗名物志》等;朱熹作有《诗集传》二十卷、《诗序辨说》等。
郑樵、朱熹二人均秉持“尽信书不如无书”的态度,大胆怀疑汉儒对《诗》的阐释。郑樵以为“《诗》《书》可信,然不必字字可信”。他否定《诗序》为子夏作,以为是“村野妄人”所作。他批驳《诗序》的“美刺说”,在一定程度上推翻了《诗序》强加于《诗》的封建说教。
朱熹接受了郑樵的一些观点,把以前遵从《诗序》而作的《诗集传》全部废弃,另作反《诗序》的《诗集传》和《诗序辨说》。朱熹自述:“《诗序》实不足信。向见郑渔仲有《诗辨妄》,力诋《诗序》,其间言语太甚,以为皆是村野妄人所作。始疑之,后来仔细看一两篇,因质之《史记》《国语》,然后知《诗序》之果不足信。因是看《行苇》《宾之初筵》《抑》数篇,《序》与《诗》全不相似。以此看其他《诗序》,其不足信者煞多。”
二人不仅大胆质疑,而且科学求证。郑樵发现《诗序》作伪的方法,即文献中虽对某君事迹无明文记载,也可依据某君的谥号来确定美刺;郑樵考论《诗》在声不在义,《诗》的起源与“乐”相联系,“乐以诗为本,诗以声为用”;孔子编《诗》与“礼”有关,可供燕享、祭祀之用,“而非用以说义也”;孔子教学《诗》,“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不是要从《诗》中求义。郑樵认为,人们不能完全认识《诗》是因为“以大小序与毛郑为之蔽障也”,而村里陋儒“乱先王之典籍,而纷惑其学,使后学不知道之大体,自汉儒始”,因此应摒弃被一度视为权威的《诗序》、郑笺,将《诗》作为诗歌看待,作为音乐看待,还原《诗》的本来面目。
郑樵这一观点也为朱熹所接受,朱熹曾说:“刺诗无所据,多是世儒将他谥号不美者挨就立名尔,今只考一篇见是如此,故其他皆不可信。”朱熹解诗也多从诗意本身出发,“解诗人本意”,不牵强附会,他说:“曾有一老儒郑渔仲更不信《小序》,只依古本与叠在后面。某今亦只如此,令人虚心看正文,久之其义自见。盖所谓《序》者,类多世儒之误,不解诗人本意处甚多。”
郑樵《诗辨妄》一石激起千层浪,遭到了守旧派的大肆攻讦。淳熙间,周孚作《非诗辨妄》“凡四十二事,为一卷”,择取郑氏书中51条进行反驳,代表了学术保守派的立场。就在这时,朱熹挺身而起,依郑樵之说而作《诗序辨说》。《诗序辨说》作于周孚《非诗辨妄》之后,朱熹在序中说:“近世诸儒多以《序》之首句为毛公所分,而其下推说云云者为后人所益,理或有之。但今考其首句,则已有不得诗人之本意而肆为妄说者矣,况沿袭云云之误哉!”旗帜鲜明地指出宋代文人比较相信的《诗经》各诗小序的首句也有“不得诗人之本意而肆为妄说者”。
事实上,郑樵、朱熹的说《诗》方式是正确的,著名史学家顾颉刚先生曾作《〈非诗辨妄〉跋》指出周孚墨守成规,所论大多为无稽之谈,而郑樵确有真知灼见。他赞赏郑樵:“社会上用了很冷酷的面目对他,但他在很艰苦的境界里,已经把自己的天才尽量发展了,我们现在看着他,只觉得一团饱满充足的精神,他的精神不死。”
是的,历史川流不息,精神代代相传。郑樵、朱熹二人无论生前会面与否,均不妨碍二人开拓创新、质疑实证精神的代际传承,也不妨碍勇敢创新精神在八闽大地的薪火相传。
(作者单位:福建省委党史方志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