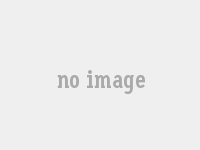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随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不断深入人心,我国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取得重大成效,大量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种群实现恢复性增长。野生动物保护法网涵盖行政、民事、刑事等多元法律规制,刑法保护是其中最具威慑力的一环,基于此,笔者拟从法益甄别、谦抑性原则适用与预防性规制三个维度,就野生动物刑法保护的体系化完善提出建议,助力野生动物刑法保护紧跟时代需求,实现生态保护与法治建设的协同共进。
法益甄别的范式转换:从秩序本位到生态安全
法益理论作为环境刑法体系建构的基石,其内涵变迁深刻影响着野生动物刑法保护的规范逻辑。传统人类中心主义法益观将刑法保护范畴限定于人身财产利益,范围狭窄,难以回应生态系统整体性保护的现实需求;而生态中心主义法益观过度强调生态伦理,以生态学的环境利益为刑法保护的核心,与法律作为人类社会规范的属性并不相符。生态学的人类中心主义法益观在一定程度上考虑了环境对人类的长远影响,更加注重人类与环境的相互关系,强调在保护人类利益的前提下,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适应现代的生态文明社会建设实践,逐渐成为当下的主流观点。具体到野生动物的刑法保护法益中,生态安全法益观的提出,实现了从“人类利益优位”向“生态—人类利益衡平”的范式转换,既强调生物多样性、生态平衡等集体法益的基础价值,又注重公共卫生安全等个体法益的延伸保护。
刑事立法沿革亦清晰展现了这一转型轨迹:1979年刑法侧重对野生动物资源管理秩序的维护,2020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将公共卫生安全纳入保护范畴,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设非法猎捕、收购、运输、出售陆生野生动物罪,标志着法益体系已形成“生物多样性维护+公共卫生风险防控”的双层结构。司法实践中,非法狩猎罪与该新增罪名的界分,正是通过判断行为侵害的主导法益类型实现——前者侧重野生动物资源保护,后者偏重公共卫生风险防控。这种法益分层机制既契合生态学的人类中心主义的理论内核,也符合风险社会刑法功能扩张的现实需要。值得关注的是,生态安全法益观的司法适用仍面临诸多现实问题,例如物种疫源属性判断标准缺失、生态损害量化评估困难等。对于物种疫源属性判断可构建“基因测序+流行病学”的复合认定体系。基于生态损害难以量化的实际困境,可以刑法所保护的法益为甄别标准,以经过科学论证的野生动物在生态系统中的作用为主要评估依据,以经济价值为辅助判断标准进行综合评估。在野生动物的刑法保护中坚持法益保护原则,不仅有助于刑事立法的完善,而且有利于刑事司法的适用。明确不同野生动物犯罪个罪所侵害的法益能够有效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是贯彻刑法谦抑性原则的基础。
谦抑性原则的双重面向:立法克制与司法限缩
刑法谦抑性原则在野生动物保护领域呈现“立法积极化”与“司法审慎化”的辩证统一。有学者提出的“立法扩张与司法限缩相统一”理论框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立法层面通过增设抽象危险犯扩大犯罪圈,司法层面则需通过实质解释限缩处罚范围。这种动态平衡在刑法修正案(十一)中得到充分体现——立法扩张表现为食用目的行为犯罪化,司法限缩则要求严格把握“情节严重”的实质危害性。
具体适用中需重点解决三类问题:其一,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认定。司法解释以直接采用《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的规定作为认定依据,虽然能解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司法认定的问题,但随着野生动物的变化,面临着名录更新不及时的现实问题。有关野生动物的认定还需要实事求是地进行与时俱进地更新。特别是在实践中广泛存在着对人工繁育物种的认定困惑与争议,可以采取差异化的认定标准,建立“繁育技术成熟度+生态影响评估”的双重标准,对技术成熟、种群稳定的人工种群实行梯度保护。对于具有成熟养殖技术的物种,可探索建立“白名单”制度,而一些尚未突破人工繁育技术瓶颈的物种则需从严管控。其二,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的衔接。实证研究发现,在涉及野生动物的刑事案件中,行为人多为初犯、偶犯且缺乏对野生动物保护的认识,社会危害性较小且再犯可能性较低。对于初犯、偶犯且未造成实质危害的行为,可恪守“前置法优先”原则,通过建立行刑衔接“缓冲带”避免刑事打击泛化。其三,违法性认识错误的司法认定。野生动物的相关专业知识问题并非日常生活的常识,具有极强的专业性。司法实践中,部分司法机关在办理涉及野生动物保护案件时,过度依赖《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展开裁判,仅依据名录认定行为违法性,忽视对行为人违法性认识可能性的实质审查。因此,在涉及野生动物的刑事案件中就违法性认识错误的认定,需构建“常识认知+公示程序+专业咨询”的综合判断标准。
预防性规制的边界探索:风险防控与自由保障
预防性刑法观在野生动物保护领域的运用,体现为危险犯设置前移与保护范围拓展。这种立法转向具有三重正当性基础:生态损害的不可逆性要求刑法提前介入,生物安全风险的扩散性需要制度性防控,环境治理的系统性呼唤法律协同。例如,在全国首例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绿孔雀案”中,法院判决停止将淹没绿孔雀栖息地的水电站项目建设,提前规避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重大风险,是通过积极预防保护野生动物的正面示范。
预防性规制呼应了刑法的法益保护原则。法益保护原则为预防提供了实质性的内容,明确了野生动物保护的对象范围,并且通过预防实现法益保护的目标。不仅如此,它有利于贯彻刑法的谦抑性原则。通过规制潜在高危行为,减少刑法可能的介入。通过提前防控避免危害结果扩大,降低刑罚扩大化的风险。这与谦抑性原则的目的相契合。刑法是社会治理的重要部分,但不是唯一手段。刑法为构建生态文明社会提供保障,尤其是在前置法难以独立保护的情况下发挥着无法取代的作用,这是刑法介入野生动物保护的正当性所在。在野生动物保护领域,刑法坚持预防性原则能够有效规制危害行为,引导公众树立正确的保护意识。随着社会的发展,公众对生态与野生动物保护的意识及期望不断提升,预防性原则顺应这一趋势,通过维护公共利益和生态安全,进一步增强公众对法律的信任以及对保护工作的支持。但预防性规制须严守法治边界:其一,危险性判断需遵循“科学证据+比例原则”。其二,行刑衔接需构建“预警—响应—反馈”机制。可通过建立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平台,实现行政监管信息与刑事司法数据的实时共享。其三,责任形式可创新“生态修复+行业禁止”的复合模式,并创新代际衡平的责任承担机制。将野生动物的保护作为系统性工程推进,将栖息地修复、种群复壮等生态补偿措施纳入刑事责任体系。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于2017年12月印发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方案》的深化实施,为将生态修复效果纳入刑事责任评价提供了制度接口。
野生动物刑法保护的现代化转型,需要构建“法益分层识别—谦抑动态平衡—预防适度扩张”的三维治理框架。在规范层面,应推进野生动物保护法与刑法的衔接修订,明确“珍贵、濒危”的动态认定标准,建立“生态价值+种群数量+分布范围”的三维评估体系;在机制层面,需完善行刑衔接程序与生态损害赔偿制度,构建覆盖“监测预警—快速反应—损害评估—修复执行”的全链条治理体系;在价值层面,须平衡生态安全维护与经济社会发展,建立“重点保护区—适度利用区—人工繁育区”的梯度管控模式。唯有如此,方能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与风险社会治理间求得最大公约数,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坚实刑法保障。
(作者分别为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