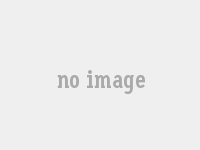转自:中国环境网
在青藏高原的腹地,一场场惊心动魄的生命保卫战正在书写新时代的生态史诗。
守护者们用毛毯裹住的不只是受伤的雪豹,更是对万物有灵的古老智慧的传承;他们追击流浪狗护卫的不只是普氏原羚,更是对生态安全底线的坚守;他们怀抱岩羊幼崽传递的不只是体温,更是对生命共同体理念的生动诠释。
当全球生物多样性丧失速率不断加快,青海用39.08%国土面积纳入自然保护地的壮举,以国家公园示范省建设的创新实践,在地球第三极竖起生命共同体的中国标杆—3400只普氏原羚种群恢复的曲线,雪豹频繁现身红外相机的画面,岩羊种群逐年增长的数据,都在诉说着高原守护者如何用脚步丈量信仰,用体温焐热希望。
今天的青海,胸怀“国之大者”,在平均海拔4000米的“世界屋脊”上筑起生命防线,用行动诠释着:守护生物多样性不仅是对自然规律的敬畏,更是人类文明存续的必答题。
24小时·雪山之王的生命接力
“索加乡发现受伤雪豹,立即组织救助!”
3月4日正午,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长江源(可可西里)园区国家公园管委会治多管理处生态保护站的欧项旦巴接到站长肖虹的紧急来电。此刻,距离治多县城250公里的索加乡——这个被誉为“天边的索加”的三江源国家公园核心区,正上演着一场与时间赛跑的生命急救。
医护人员为雪豹检查身体 欧项旦巴供图
搁下未吃完的午餐,欧项旦巴与同事火速启程。笔直的柏油路在苍茫的高原草甸上无尽延伸,越野车卷起的烟尘里裹挟着救援人员的焦灼:“小家伙,一定要挺住!”
下午5时,两人终于赶到索加乡政府所在地,与派出所民警、生态管护员会合后,带了一条毛毯,前往雪豹受伤的地方。
前往索加乡救助受伤雪豹 欧项旦巴供图
“以前培训时,培训了如何救助受伤的野生动物,需要找件衣服或者毯子,将受伤野生动物的头盖住,以免出现应激反应,造成伤势加重或者攻击救助人员。”欧项旦巴说。
受伤雪豹的位置在一处山腰,山体颜色与雪豹身上的毛色别无二致,直到走到雪豹跟前,欧项旦巴才发现受伤的小家伙躺在地上一动不动。
看到救助人员后,雪豹只是艰难地动了一下嘴巴,眨了一下眼睛,就这样简单的动作,似乎都耗尽了雪豹所有的气力,昔日“雪山之王”的威仪此刻化作令人揪心的孱弱。
几人将雪豹放在毛毯上,轻轻抬到山下,从小卖部买了一袋牛奶,慢慢滴到雪豹嘴里,小雪豹艰难地咽着。
晚上11时左右,欧项旦巴带着雪豹赶到治多县城,县畜牧兽医站工作人员早已等候,为雪豹检查身体,并与青海野生动物救护繁育中心专家远程视频诊断,确定受伤雪豹为一只幼崽,后腿有明显外伤,受伤原因不明,5天时间未进食。专家一致决定,将雪豹送往青海野生动物救护繁育中心救治。
子夜时分,载着雪豹的救援车再度启程。1000多公里高原夜路,欧项旦巴与同事更尕陈林轮番驾驶,每隔几个小时停车为雪豹补充葡萄糖和牛奶。巴颜喀拉山的凛冽寒风、鄂拉山口的急弯陡坡、共和县城的朝阳,见证着这场持续24小时的爱心接力。
时间就是生命,3月5日正午,青海野生动物救护繁育中心大门开启的瞬间,彻夜未眠的两位高原汉子终于舒展眉头。
启示:这场跨越千里的生命接力,不仅是对濒危物种的生死守护,更是对三江源生命共同体最生动的注解。从管护员发现到汇报,从国家公园工作人员赶赴现场救助到省级专家远程会诊,每一个环节都闪烁着现代生态治理的智慧光芒。雪豹作为高原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它的生机与危机都是青藏高原生态健康的晴雨表。当人类怀着敬畏之心为野生动物让渡生存空间,当科技力量与传统经验在生命救援中交织辉映,生态文明的理念已化作温暖而坚韧的守护之光。愿雪山之王矫健的身影,永远奔腾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壮美画卷中,祈愿小雪豹尽快康复。
追击战·普氏原羚的生死突围
“这些流浪狗比狼群还凶!”海北藏族自治州刚察县哈尔盖镇环仓秀麻村村民杰日贡红着眼眶数着草原上羊羔的尸体。去年,他家20多只新生羊羔命丧犬牙,这样的惨剧正在青海湖畔的哈尔盖镇上演。
2024年,哈尔盖镇流浪狗“流窜作案”,袭击羊羔,甚至威胁人身安全,牧民苦不堪言,却又无可奈何。
然而,这样的问题同样困扰着哈尔盖保护站负责人郭晶,“流浪狗不仅咬死咬伤牧民家畜,更可恶的是还会围猎普氏原羚。”
普氏原羚是中国特有物种,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青海湖环湖地区是普氏原羚的唯一栖息地,目前数量为3400余只,其中三分之二栖息在哈尔盖镇辖区内。因数量稀少,普氏原羚也被称为“奔跑在草原上的大熊猫”。
因此,对于哈尔盖镇保护站而言,天大的工作就是普氏原羚的保护和监测。
“如今,牧民对于普氏原羚的保护意识非常强,把它们看得比自家牛羊还金贵。而普氏原羚在辖区最大的威胁是流浪狗群。”说起流浪狗,郭晶深恶痛绝。
去年,哈尔盖保护站与当地镇政府、派出所建立协作机制,共同守护普氏原羚。通过前期摸排追踪流浪狗活动轨迹,排除23只流浪狗的侵扰,普氏原羚种群获得了短暂的安宁。
今年春节时,新犬群如同幽灵,出现在草原上,既袭击牧民羊羔,又围猎珍稀的普氏原羚。
2月8日的紧急呼叫揭开人犬鏖战的序幕。当天,察拉村牧民阿多放牧时,发现流浪狗围猎一只普氏原羚。普氏原羚“突围”流浪狗包围圈时,不慎挂在网围栏上。
阿多驱赶流浪狗后,将受伤的普氏原羚送到哈尔盖镇派出所,派出所民警将郭晶叫过去一同处理。
救助受伤的普氏原羚 郭晶供图
“我们现场观察诊断,发现这是一只成年雄性普氏原羚,伤情严重,四肢多处有咬伤,头部下颚骨肉分离,无法站立。”郭晶当天下午就将受伤的普氏原羚送往青海野生动物救护繁育中心救治。
哈尔盖保护站负责区域东至哈尔盖河,沿315国道一直延伸至沙柳河东岸,管辖面积1200多平方公里。哈尔盖地区有5个普氏原羚种群,其中就有4个在哈尔盖保护站区域内,因此保护好普氏原羚任务艰巨。
“没想到刚消停了几个月,流浪狗群又开始流窜,我们也要开始准备新一轮的抓捕行动了。”郭晶望着远处雌性普氏原羚渐渐隆起的肚子说,要赶在今年普氏原羚产羔季前,将流浪狗这个威胁铲除掉,还普氏原羚安宁的生存家园。
启示:当祁连山的季风掠过青海湖畔,普氏原羚跃动的身影与牧民转场的牛羊共同勾勒出生态共同体的鲜活图景。这场人犬鏖战背后,折射的不仅是物种存续的危机,更是现代文明对荒野责任的重新审视——被遗弃的宠物犬异化为“生态杀手”,而普氏原羚却在牧民自发的守护中重获生机。从保护站监测相机里新增的幼羚影像,到牧民将受伤羚羊紧抱怀中的体温,每一个生命突围的瞬间,都在诉说着:荒野从来不是人类的独奏舞台,唯有以谦卑之心编织守护之网,方能听见万物共生的和鸣。
归群记·岩羊孤羔的荒野重生
在祁连山脉银装素裹的怀抱中,一只棕白相间的小岩羊最后一次蹭了蹭郑伟国的手掌,随即转身跃入苍茫雪原。
春节前夕,这个被取名为“一一”的7个月大幼崽,在经历30多天特殊的“托育”后,重返自然家园。看着小家伙跑远,郑伟国恋恋不舍地返回,脸上满是不舍。
“救助的最终目的就是回归自然,如果一直待在管护站,反而会害了小岩羊。”郑伟国说。
时间倒回至2024年12月中旬,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硫磺沟管护站站长郑伟国在零下20℃的风雪中,发现这只与羊群失散的幼崽。小岩羊蜷缩成一团,趴在草地上冻得瑟瑟发抖,郑伟国脱下身上的棉衣,将小岩羊包裹好,带到管护站救助。
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硫磺沟管护站站长郑伟国清楚,没有母羊哺育的岩羊幼崽,在冬季存活率不足10%。
硫磺沟管护站地处海北藏族自治州门源回族自治县皇城乡大梁,距门源县浩门镇60公里。硫磺沟管护站管护区域内有丰富的野生动植物资源。
从此,这个海拔3345米的管护站,多了一位特殊“住客”。工作人员自掏腰包购置袋装牛奶喂养小羊,“起初,小羊还不肯喝,我们只能小心翼翼地掰开小羊的嘴巴,用勺子轻轻地喂进去。”
硫磺沟管护站工作人员喂养救助的小岩羊 郑伟国供图
令人称奇的是,这只本该怕生的小岩羊,竟把郑伟国当成了“代理家长”——清晨会轻叩宿舍门讨奶喝,白天跟着郑伟国,咬咬裤脚“求抱抱”。
“它就像个跟屁虫,连我们开会都要卧在脚边。”郑伟国笑着回忆,小羊对管护站的依恋催生了“一一”这个特别的名字——既是建站以来首例长期救助案例,更寄托着从一到万的生态愿景。
“这些年,管护站每年都会救助野生动物,受伤的草原雕、狍子、岩羊……伤情不严重的话,简单包扎或者喂养两三天后就会放归,伤情严重的直接送到祁连山国家公园野生动物救护繁育站救助,很少有野生动物能长时间待在管护站。只有这只小岩羊是个例外,我们在管护站喂养了一个多月。”郑伟国说。
放归当天的场景让所有巡护员红了眼眶:本可径直入山的小家伙,每跑十几米就驻足回望。当“一一”跃入山野的背影与天际线重合,我们看到的是生态文明最生动的注脚。
启示:当硫磺沟的暴雪模糊了物种的边界,人类掌心托起的不只是颤抖的幼小生命,更是荒野法则与文明温度的和解密码。从蜷缩在棉衣里的脆弱生灵,到雪原上纵跃的矫健身影,“一一”的三十多天托育史,恰是生态修复最精微的刻度——那些深夜温热的奶瓶、散落在院子里的粪球,都在重构着人与自然的关系图谱。当小岩羊最后一次回望的身影刺破寒雾,我们终于读懂:所谓守护,不是以爱为名的禁锢,而是让每个生命都能在风雪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族群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