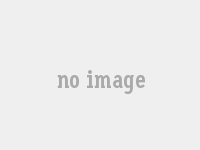熊锦秋
近日证监会发布《证券投资基金托管业务管理办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下称《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笔者对此提些个人浅见。
《意见稿》修订的内容,主要包括完善准入门槛,强化实质展业、风险隔离监管要求,压实托管人责任,健全退出机制,允许优质托管机构设立全资子公司专门从事托管业务等。
在基金投资运作过程中,基金托管人的作用非常重要,最显著的一条,就是安全保管基金财产、防止基金管理人卷款跑路。除此之外的职责还包括“复核、审查基金管理人计算的基金资产净值和基金份额申购、赎回价格;监督基金管理人的投资运作”等。此前个别私募基金出现管理人掏空基金资产等问题,其中托管人没有履行好相应职责并发挥好作用是一个主因。
分析深层次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其一,基金托管费旱涝保收现象更为严重。托管费通常按照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一定比例计提,按月支付,基金收益如何、甚至出现什么问题,托管人基本都照收不误。
其二,托管人对管理人的投资监督权,在法律条款和实践中并未理顺。《基金法》第37条规定,托管人发现管理人的投资指令违反法律法规和其他有关规定,或者违反基金合同约定的,应当拒绝执行。另外《意见稿》也明确了托管人的投资监督权。但对股票内在价值的评判,各方观点并不同。亏损股市值比绩优股市值高,实践中个别基金管理人以高价买入新三板等个股、为第三方定向输送利益,对这些问题,托管人如何认定其投资指令违法违规?
而且《基金法》第36条规定托管人有一个职责是“根据基金管理人的投资指令,及时办理清算、交割事宜”,也即按此条托管人对管理人交易指令似乎只有事后审核的权利,难以在事前拒绝执行管理人的投资指令;或者说托管人对交易指令只有形式审核、而无实质审核权利。第36条与37条似难两全。另外,托管人一般由管理人来选择,托管人履行投资监督的意愿也不强。
其三,对托管人法律责任不好追究。按《基金法》第145条,托管人在履责中违反本法规定或基金合同约定,给基金财产或基金份额持有人造成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但如上分析,托管人的投资监督权本就模糊不清,因此要追究由此导致的法律责任或也不易。
针对上述问题,结合《意见稿》修订,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首先,对私募投资基金应强制由托管人托管。《基金法》第50条规定公募基金应当由基金托管人托管。而按《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及《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条例》,私募投资基金并非强制托管,对于不托管情形,应当在基金合同中明确保障私募基金财产安全的制度措施和纠纷解决机制。在笔者看来,托管相比其它方式更有利于保障基金投资者利益,只有强制托管,托管人的投资监督权才可充分发挥。
其次,赋予托管人对管理人的实质投资监督权。只有规定托管人对管理人投资指令拥有事前审核、实质审核的权利,投资监督权才是实打实的,《基金法》《意见稿》等对此应予明确。为保护基民利益,由托管人放弃一些貌似诱人的投资机会也是值得的。管理人与托管人签订托管协议,其中可约定托管人投资监督程序、如何认定涉嫌违法违规投资指令等具体事项。
如果托管人的投资监督权得以明晰,托管人也就需要按照《基金法》第145条承担与此相关的民事责任。而托管费也同样可以建立浮动费率机制,与托管人履责情况挂钩。
再次,完善私募基金信息披露制度。此前出现私募基金净值造假现象,但基金到底有多少资产、价值几何,托管人最清楚不过,且托管人一般并无对基金净值造假意愿。可以规定,私募基金通过法定信披渠道披露信息,以及在第三方平台披露的净值信息,必须由托管人复核确认、并由托管人直接提供。
本版专栏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文章来源:证券时报)
(原标题:1【头条评论】 基金托管人对管理人投资监督权应落到实处)
(责任编辑:126)